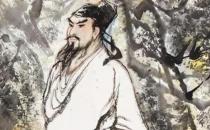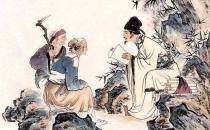三國新論 諸葛亮一手造就馬謖之死?
劉備臨死之前,曾經(jīng)告誡過諸葛亮:“馬謖言過其實(shí),不可大用。”但諸葛亮似乎將劉備的諄諄告誡當(dāng)作了耳旁風(fēng),左耳進(jìn)、右耳就出去了。韜光養(yǎng)晦已久,至關(guān)重要的首次北伐,諸葛亮就重用了馬謖,“時(shí)有宿將魏延、吳壹等,論者皆言以為宜令為先鋒,而亮違眾拔謖”。最后恰如劉備所擔(dān)心的那樣,馬謖在街亭(今甘肅省秦安縣隴城鎮(zhèn))一意孤行,舍水上山,犯了兵家之大忌,結(jié)果被張?截?cái)嗔思乘溃夥陸K敗,部眾四散流離。首次北伐的大好局面就此發(fā)生扭轉(zhuǎn),諸葛亮損兵折將,只得無功而返。
諸葛亮素有知人之明,卻在馬謖問題上犯下了這樣的錯(cuò)誤,歷來為史家所感嘆。諸葛亮揮淚斬馬謖以謝眾人,習(xí)鑿齒(東晉文學(xué)家、史學(xué)家)就此發(fā)表議論:“諸葛亮不能兼并上國,豈非理應(yīng)如此……蜀漢僻陋于一方,人才少于上國,而諸葛亮殺其俊杰,以求收到其他人的駑鈍之用,希望以此成就大業(yè),不亦難乎!而且先主曾經(jīng)告誡過馬謖其人不可大用,豈不等于早就鑒定出了馬謖并非什么人才了嗎……如果諸葛亮知道馬謖不可大用而用之,則違背了明主之誡;如果說對馬謖的裁決有失公允,那就意味著他殺了有益之人。無論如何,在這件事情上,諸葛亮都很難稱得上是一個(gè)智者。”
事實(shí)上,馬謖之死遠(yuǎn)遠(yuǎn)沒有我們通常印象中所知的那么簡單,這其中牽涉到蜀漢集團(tuán)內(nèi)部一場巨大的權(quán)力轉(zhuǎn)移。劉備生前,蜀漢集團(tuán)存在著四大軍區(qū):荊州軍區(qū)的關(guān)羽軍團(tuán),漢中軍區(qū)的魏延軍團(tuán),永安?江州軍區(qū)的李嚴(yán)軍團(tuán),京畿軍區(qū)的劉備直屬軍團(tuán)。后來關(guān)羽軍團(tuán)徹底覆敗,只剩下三大軍團(tuán)。李嚴(yán)直轄永安?江州軍團(tuán)的同時(shí),擁有著對其他諸軍團(tuán)的節(jié)制權(quán)。
諸葛亮南征平叛所率部隊(duì),主要來自京畿軍團(tuán)??李嚴(yán)在諸葛亮南征期間不聞不問,永安?江州軍團(tuán)諸葛亮自然無法號令;漢中魏延軍團(tuán)身處前線也不可能抽得開身。南征的意義也正在于,諸葛亮從此將京畿軍團(tuán)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。建興六年的首次北伐,除了前面我們所講到的:為了攻取涼州或者涼州的一部分,為蜀漢集團(tuán)尋求一塊出川的跳板這一戰(zhàn)略目的之外,還有一個(gè)重要目的,那就是借此控制漢中軍區(qū)的魏延軍團(tuán)。
魏延雖然是荊州人氏,但他卻是劉備的部曲將(家將),從來就不屬于諸葛亮一系。劉備用魏延鎮(zhèn)守漢中而不用閑得發(fā)慌的名將張飛,其著眼點(diǎn)就在于魏延這個(gè)“家將”的身份。諸葛亮在蜀漢集團(tuán)內(nèi)部費(fèi)盡心機(jī)進(jìn)行的權(quán)力轉(zhuǎn)移行動(dòng),自然也少不了對魏延及其漢中軍團(tuán)的處理。
建興五年,諸葛亮打著北伐統(tǒng)帥的旗號順理成章地進(jìn)駐漢中,從此魏延徹底告別了鎮(zhèn)守漢中的方面軍軍事將領(lǐng)的身份,而蛻變成為諸葛亮麾下的一員偏將。此后,魏延頭上先后被冠以這些職務(wù)和爵號:(北伐軍)前部督、領(lǐng)丞相司馬、涼州刺史、前軍師、征西大將軍、假節(jié)、南鄭侯。他再也沒有機(jī)會(huì)去實(shí)踐他在劉備面前許下的豪言壯語:“若曹操舉天下而來,請為大王拒之;偏將十萬之眾至,請為大王吞之。”
諸葛亮違眾起用名不見經(jīng)傳的馬謖擔(dān)任首次北伐的先鋒,而棄用名將、宿將魏延和吳壹(吳壹之妹為劉備夫人,吳壹也非諸葛系之人),其背后的用心實(shí)在良苦。諸葛亮剛剛變相地順利接收了漢中軍團(tuán),他并不想立刻給魏延立功的機(jī)會(huì),他想把這個(gè)機(jī)會(huì)留給自己的親信馬謖??馬謖自謂“明公視謖猶子,謖視明公猶父”,可見二人關(guān)系的不同尋常。馬謖出任先鋒,和諸葛亮刻意在軍中培養(yǎng)親自己的軍事將領(lǐng)的目的是一致的。此次北伐,形勢本來已經(jīng)甚好,只要馬謖能夠穩(wěn)重持中,不出紕漏,根本不需要他有什么突出的精彩表現(xiàn),諸葛亮扶植他的目的就能達(dá)到。但是天算不如人算,馬謖竟然慘敗于街亭。
至此,馬謖只能一死。準(zhǔn)確地說:諸葛亮只能選擇讓馬謖一死。
因?yàn)橛民R謖而不用魏延,是諸葛亮獨(dú)排眾議的決定,諸葛亮必須就此負(fù)責(zé)。在諸葛亮上奏給劉禪的《自罪疏》中,有這樣的句子:“臣明不知人,恤事多暗,《春秋》責(zé)帥,臣職是當(dāng)。請自貶三等,以督厥咎。”不過,如果僅僅因?yàn)檫@一原因,諸葛亮大可自己多承擔(dān)些責(zé)任,馬謖尚且用不著去死。
最關(guān)鍵的是,令馬謖出任北伐軍先鋒的背后,隱藏有諸葛亮不可為他人道的政治陰謀。這就是諸葛亮在軍中培植自己勢力,削弱劉備時(shí)代的功臣元老。雖然事情做得隱蔽,但蜀漢集團(tuán)內(nèi)部也難免有人就此說三道四。馬謖勝利了則萬事大吉,諸葛亮也可以免遭任人唯親之嫌,相反,可獲任人唯賢之名,馬謖也可以就此順利進(jìn)入軍中擔(dān)任要職;馬謖一旦覆敗,諸葛亮必然會(huì)招致海量非議,倘若馬謖再獲得從輕發(fā)落,輿論必然會(huì)朝著更加不利于諸葛亮的方向發(fā)展,唯有對馬謖施以最重的處分?jǐn)厥祝侥芷较⑹駶h集團(tuán)內(nèi)部鼎沸的議論。
故而從一開始,馬謖這個(gè)先鋒就處于只能取勝、不能戰(zhàn)敗的逆境。為了諸葛亮的政治利益,丟失街亭的馬謖必須去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