張學(xué)良在臺(tái)灣的幽禁歲月 活動(dòng)區(qū)域只有200米
張閭蘅是張學(xué)良五弟張學(xué)森之女,她1967年從美國留學(xué)回來后先在香港工作了幾年,又回臺(tái)灣住了一段時(shí)間。張學(xué)良的子女都不在身邊,她與妹妹張閭芝便成了大伯張學(xué)良關(guān)系最親密的家人,見證了張學(xué)良在臺(tái)灣的幽禁歲月。
第一次看見大伯,從門縫里偷看
張學(xué)良在日記中記載,1946年11月,在不知情的情況下,他和趙一荻被秘密從重慶轉(zhuǎn)移到了臺(tái)灣,自此進(jìn)入了更秘密的幽禁,先是在新竹縣井上溫泉,住的是日本人設(shè)計(jì)建造的木板房,舊式木板房里只有簡單家具,冬天潮濕陰冷。夏天稍遇大雨便四處漏水。周圍都是臺(tái)灣山地原住民,他們平時(shí)不能隨便越過警戒線。井上溫泉與外界只有一條公路,路面損壞嚴(yán)重,如果遇到暴風(fēng)雨,人和車都無法通行。
1949年2月2日凌晨3點(diǎn),張學(xué)良又被突然轉(zhuǎn)移到高雄,秘密藏在壽山要塞的兵舍中。當(dāng)時(shí),“代總統(tǒng)”李宗仁要求“恢復(fù)張、楊自由”,毛人鳳等借口不知“張、楊”在何處,推托不辦。盡管各界呼聲甚高,但沒有“蔣先生”點(diǎn)頭,自然無人去落實(shí),故一拖再拖,終成一紙空文。而張學(xué)良、趙一荻被囚禁于臺(tái)灣井上溫泉已被外人知曉,為了“安全”就把他們緊急轉(zhuǎn)移至高雄。
張學(xué)良在金山觀海
在高雄住了近一年,因?yàn)閾?dān)心高雄已成為空襲目標(biāo),1950年1月,張學(xué)良又搬回井上溫泉,從此開始了長達(dá)十余年的井上幽禁歲月。
井上溫泉遠(yuǎn)離城鎮(zhèn),采購困難。“大伯靠自己種點(diǎn)青菜、養(yǎng)些雞鴨才得以維持簡單的營養(yǎng)。本是大家閨秀的大媽關(guān)在山里,那段日子生活很艱苦,沒有衣服穿,都是我大媽自己做的。那里連電燈都沒有,幾年里,大伯聽力、視力大為減退。他的精神也很苦悶,有時(shí)只能逗小貓打發(fā)時(shí)間,一點(diǎn)娛樂都沒有。”張閭蘅回憶起伯父的這段歲月,感慨萬千。
但是張閭蘅并不是一開始就知道自己有個(gè)大伯和大媽住在新竹縣竹東的一個(gè)人煙稀少的山里。
“我第一次見到我的大伯、大媽大概在1954年。”那一年,張閭蘅在臺(tái)灣上小學(xué)五年級(jí)。有一天,接她上下學(xué)的三輪車夫給了一張紙條,紙條是媽媽讓閭蘅放學(xué)后直接到臺(tái)北中心診所找她。
到了之后,她發(fā)現(xiàn)全家人都在診所,等待著張學(xué)良和趙一荻的到來,一聽到廊道有動(dòng)靜,家人都貼在門縫往外看。媽媽告訴閭蘅:“大媽生病要住院開刀,大伯、大媽從山里來到臺(tái)北。”但是這一次,小閭蘅并沒有和大伯、大媽直接碰面,而是偷偷地看,“我只是看清了大媽的模樣,而大伯只看見了背影。”張閭蘅說。
只有200米活動(dòng)區(qū)域
張閭蘅上高中時(shí),大伯、大媽從高雄搬回臺(tái)北,但還是不允許與家人見面。“記得一個(gè)星期天,迪克(盧致德)約我們一家去做客,他家隔壁住著董顯光(原“國民黨駐美大使”),聽說那天大伯、大媽會(huì)到董顯光家做客,這次,我們是隔著大玻璃窗觀望。”張閭蘅至今還記得那次終于看清了大伯的模樣:“個(gè)頭不太高,有些發(fā)福,頭發(fā)灰白,幾乎掉光了,怎么也想象不出當(dāng)年英俊少帥的樣子。”
1965年,從美國留學(xué)返臺(tái)省親,張閭蘅在家中與大伯、大媽第一次真正見了面。張學(xué)良和趙一荻搬到臺(tái)北后,在北投復(fù)興崗建房,與過去相比稍許自由些,大伯到臺(tái)北市區(qū)總會(huì)來她家里坐坐。
“大媽話不多,眼神中總有一絲淡淡的憂郁。她很少向外人提及自己的內(nèi)心感受。”趙一荻是位虔誠的基督徒,大家聊天時(shí)如果大媽插話進(jìn)來,就是宣傳她的基督教。
有時(shí),張學(xué)良也不會(huì)耐煩地打斷趙一荻的話:“行了,我們在聊天呢!”
在張閭蘅眼里,大媽對大伯來說,是絕對的賢妻,他的生活就是她的全部世界。大伯談起她時(shí),有時(shí)會(huì)說:“人家對我好,我就得對人家好啊。”
1967年,張閭蘅回到臺(tái)灣。張閭蘅說,從1965年開始,大伯、大媽基本上有自由了,每星期起碼來她們家三到五次,但是每次來,總要弄出很大的動(dòng)靜。“一群時(shí)刻跟隨的‘服侍’先進(jìn)家轉(zhuǎn)一圈,看有否陌生人后,便在門外警戒,有時(shí)甚至坐在屋里,面無表情地聽我們家人聊天。”
張學(xué)良的的自由活動(dòng)區(qū)域只有200米,且只限于白天,黃昏以后便不能走出屋門。負(fù)責(zé)監(jiān)視張學(xué)良的劉乙光規(guī)定:執(zhí)行內(nèi)部警戒任務(wù)的特務(wù),白天須站在張學(xué)良住房10丈左右的位置,晚上則移至寢室窗外和門口;外圍憲兵白天在遠(yuǎn)處站崗,夜晚則移到特務(wù)們白天所站的位置放哨。在特務(wù)的警戒范圍外,憲兵連的士兵們?nèi)揭粛彛宀揭簧冢舜讼嗤纬梢粋€(gè)包圍圈。借此機(jī)會(huì),張學(xué)良的一言一行,都受到了劉乙光的監(jiān)視。
熱愛生活的“老頑童”
1962年,劉乙光調(diào)走。張學(xué)良為他舉行了“餞別”宴會(huì),參加宴會(huì)的還有蔣經(jīng)國、彭孟緝。酒席上,張學(xué)良語出驚人:“劉乙光是我的仇人,也是恩人。說是仇人,因?yàn)樗麌?yán)格看管我;說是恩人,因?yàn)樗冗^我的命(那是在貴州桐梓時(shí),張學(xué)良突發(fā)盲腸炎,在來不及請示獲準(zhǔn)的情況下,劉乙光自作主張,將張學(xué)良送到貴陽中央醫(yī)院做手術(shù)。如果劉乙光不將張學(xué)良及時(shí)送醫(yī),一旦病情惡化后果不堪設(shè)想)。現(xiàn)在他要走了,我想送他一筆錢,算是我的一點(diǎn)心意。”
“趙四小姐”趙一荻
張閭蘅平時(shí)不能常去大伯家,偶爾去了,家人總要再三交代,說話要小心,隔墻有耳,不能口無遮攔,免得給他們添麻煩。在張閭蘅看來,他們宛如生活在“鳥籠”中,“自由”是很有限的,來往的朋友也少得可憐,除了家人,只有張群、張大千、王新衡、大衛(wèi)黃(黃仁霖的兒子)等幾家可以走動(dòng)。
張學(xué)良每次外出都要提前報(bào)告,出門時(shí),總是兩輛車,前一輛是大伯、大媽,跟隨的一輛就是便衣特務(wù)或警衛(wèi)。張學(xué)良似乎已經(jīng)習(xí)慣了這種被人監(jiān)視的生活,他很坦然,依舊與張閭蘅家人大擺“龍門陣”,聊到高興時(shí),笑聲朗朗,有時(shí)候未盡興還要拉著大家一同去下館子,邊吃邊聊。
張閭蘅說,聽大伯講,他在30年代就擁有自己的私人飛機(jī),甚至自己駕駛飛機(jī)到南京開會(huì),再想想現(xiàn)在,這叫什么日子?當(dāng)年是從天上掉到地上,沒有糖吃不知道糖啥滋味,知道了什么滋味一下子沒有了,什么感受?
然而,生活中的張學(xué)良是一個(gè)睿智的長輩,一個(gè)熱愛生活的“老頑童”,言語中不失機(jī)敏活潑,有一次他請客,席上有好幾位中年太太,這些太太都是平常陪他打牌的牌友。其有人說:“大爺,這一屋子的美女陪你吃飯,您多幸福呀。”張學(xué)良馬上笑著回答:“嗯,你們都是美女,那丑人都到哪里去了?”在場的人都哈哈大笑起來。
“他內(nèi)心的痛楚,是言語無法表達(dá)的。環(huán)境、容貌都在改變,但惟一沒變的,是他性格中的開朗豁達(dá)與率真。”張閭蘅說。
與老部下在美國重逢
1911年3月10日,失去自由達(dá)半個(gè)多世紀(jì)的張學(xué)良和趙一荻,終于離開臺(tái)灣去美國探親。
同年5月23日,張學(xué)良的老部下呂正操及隨員多人,飛往美國看望張學(xué)良。這一切就是由張閭蘅負(fù)責(zé)安排的。
1991年5月29日上午,紐約曼哈頓公園大道的一棟公寓里,兩個(gè)分離了整整54年的耄耋老人雙手緊緊地握在了一起。在紐約見面那天,張閭蘅陪著呂正操乘電梯,張學(xué)良西裝筆挺地站在門口迎接遠(yuǎn)道而來的客人。
張學(xué)良和呂正操是同鄉(xiāng),在東北講武堂時(shí)他是呂正操的老師。
“老校長!”呂正操見面仍按以前的習(xí)慣稱呼張學(xué)良。在東北軍時(shí),老部下呂正操曾在張學(xué)良軍中工作10余年。
“到今天我跟你隔了54年5個(gè)月零4天沒有見!”呂正操接著說。
“看著兩個(gè)老人差不多高,頭頂都光光的,卻像孩子一樣一直手拉著手不舍得放下,特別可愛,但我看了卻直想掉眼淚。”張閭蘅回憶說,兩位老人談了很長時(shí)間,其中張學(xué)良最想知道呂老是如何打游擊戰(zhàn)的,如何打日本人的。
張學(xué)良幽默地說:“我可迷信啦,信上帝。”
呂正操隨口接上:“我也迷信,信人民。”
張學(xué)良笑道:“你叫地老鼠。”
呂正操說:“地道戰(zhàn)也是人民創(chuàng)造的嘛,我個(gè)人能干什么,還不都是人民的功勞。八百萬軍隊(duì)被我們打垮了,最后跑到臺(tái)灣。”
張學(xué)良隨即插話:“得民者昌!”
呂正操緊接著說:“那還是靠人民群眾!”
1991年6月4日下午,張學(xué)良和呂正操又相約詳談一次。張閭蘅陪同他們到中國常駐聯(lián)合國代表團(tuán)團(tuán)長李道豫大使的別墅做客。張學(xué)良給呂正操帶去了一包臺(tái)灣產(chǎn)的鳳梨酥。
張學(xué)良說:“我看,大陸和臺(tái)灣將來統(tǒng)一是必然的,兩岸不能這樣長期下去,臺(tái)灣和大陸總有一天會(huì)統(tǒng)一,這只是一個(gè)時(shí)間問題。”他還說:“愿為祖國的和平統(tǒng)一盡點(diǎn)力量,我過去就是作這件事的,我愿保存我這個(gè)身份,到那一天會(huì)用上的。我雖然90多歲了,但是天假之年,還有用得著我的地方,我很愿意盡力。作為一個(gè)中國人,我愿意為中國出力。”(呂正操,《那年我見張學(xué)良》)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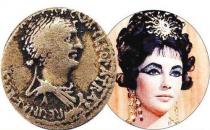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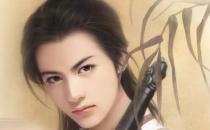


![歷史上的竇嬰是一個(gè)怎樣的人 漢武帝為什么要?dú)⒏]嬰](http://www.tewxkgs.cn/uploadfile/2019/1124/thumb_210_130_20191124112618767.jpg)


